《驾驶我的车》是村上春树的一则短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男主角家福是60岁、过了事业巅峰期的演员,因为眼疾,不得不雇佣年轻女孩渡利为他开车。工作途中,家福除了例常准备台词,空闲时不断想起亡妻。
亡妻也是演员,多年前死于癌症,她生前几度出轨,成为家福的心结,是他看似美满婚姻生活中的黑洞。家福偶然和渡利说起,他与妻的最后一任情人做过短暂的酒友,那位被家福轻视的「二流演员」,某次酒后微醺时说出:如果要窥看他人,那么只能深深地、直直地逼视自己。
![图片[1]-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b8425781j00r0nt8r000k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驾驶我的车》(2021)
这时,村上借男主角的视角写道:「这些话似乎是从这人身上某个幽深的特别场所浮上来的。尽管可能仅是一瞬之间,但他终究打开了封闭的门扇。他的话听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无遮无拦的心声。至少那不是表演。」滨口龙介在2013年读到《驾驶我的车》,对这段话印象深刻,终于在今年拍出根据小说改编的新片《驾驶我的车》。
![图片[2]-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d882fabej00r0nt8r000z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影片改变了小说中以回忆为主的倒叙时间线,几位主角的年龄较原作年轻化,细节安排也多有出入,并且融入村上另两部短篇《山鲁佐德》和《木野》的部分情节。但改编和原作的差别不构成讨论重点。
扮演家福的西岛秀俊对影片的描述很妙:「滨口导演在过往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云里雾里、彼此隔膜的亲密关系,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屡次出现肉体发生关系却心意不通的状态,所以导演很能意会村上小说的主题。但是导演有他独特的风格,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不脱离原作却拍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
![图片[3]-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2b72ca6dj00r0nt8r000x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逆光中,赤裸的女人给枕边人讲故事。女人背对爱人,对着大片窗户,窗外暮色四合,「你想知道故事的后续吗?」女人讲的是个诡异的情欲故事:女孩日复一日潜入自己暗恋的男孩家,有一天,她躺在男孩床上,听见有人开门……
听故事的男人是家福,女人是他的妻子音,是个编剧。不久之后,家福意外撞见过她和情人幽会,却不说破。某天,在夭折女儿周年祭日的法事过后,两人在漆黑的客厅里做爱,音再次讲起那个故事:女孩的前世是七鳃鳗,但她不像同类那样寄生于其它鱼类,只是吸附着水底的岩石,如柔软的水草。当她躺在男孩的床上自慰,她感到这间昏暗寂静的房间,宛如上一世的水底,时间停滞。她听到有人进门,但她期待被撞见,期待她前世的业力被终结,或许她会因此获得新生。
![图片[4]-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716f85b2j00r0nt8s000rd200hs00bug00u000jy.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七鳃鳗是被称为活化石的古老生物,形貌可怖,它们看起来像长满利齿的阴道。家福不能理解音的故事,更不能理解她的情事,但是他没有机会了——她中风猝死,留给他的只有《凡尼亚舅舅》的台词录音带。
音是盘桓于家福生活的谜中之谜。我们要在影片接近尾声时才会明白,这位床畔的山鲁佐德绝望地等待着被倾听,被看见。她发病那夜苦等丈夫时,家福逃避地躲在车库里背诵《凡尼亚舅舅》的台词:「我糊里糊涂地错过大好光阴,凡是我如今无法得到的东西在那些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得到的。」音的高深莫测的面孔将变得透明,契诃夫的文本将和家福的人生产生互文,但我们要在这些情境过去许久之后才恍悟。
![图片[5]-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76fa1c97j00r0nt8s0011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滨口曾说,观看卡萨维茨的电影时,观众往往在一个情境过去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人物之前那些神情的意味,拍摄造成演员面孔和情绪的错位,以及真实表意的「滞后」,这让他着迷,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从《欢乐时光》《夜以继日》到这部《驾驶我的车》,滨口不断地展开这类创作尝试。就像他为《夜以继日》所作的导演阐释:渴望演员进入并未在日常中呈现的,一个潜在的「赤裸世界」,不破坏现实逻辑、保证现实完整度的前提下,生出对现实似是而非的感觉。他承认,要通过电影实现这个过程,理想的状态是不存在中介,但他做不到。
![图片[6]-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aaeb1cecj00r0nt8s000ld200hs00a0g00u000gv.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夜以继日》(2018)
他在《夜以继日》里借用了《三姐妹》。到了《驾驶我的车》,他惊喜地发现小说提到《凡尼亚舅舅》,「这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我就故技重施。我重新阅读《万尼亚舅舅》,再次被契诃夫折服。万尼亚和家福在我的脑海中融合,《万尼亚舅舅》像另一部原作,在电影中占了重要位置。」
![图片[7]-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0dc7b47ej00r0nt8s001b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滨口龙介对契诃夫的依赖,远远超过对村上原作的需要。
影片和原作小说的关系,在40分钟的序幕部分就基本结束了。之后近两个半小时的影片正文,一句话总结主线:一个因为私人原因、无法再扮演「凡尼亚舅舅」的优秀演员,怎样以导演的身份带着不同国家的演员排练《凡尼亚舅舅》,历经各种意外波折,他本人最终走出内心的迷宫,再次以「凡尼亚」的身份在舞台上达成自我和解。这电影最浅表是村上的小说情节,深入下去,是契诃夫的精神意志,在最深深处,是滨口用他个性化的视听表述,表达对文本、对表演、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思考。
![图片[8]-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7f9fd15dj00r0nt8t002hd200u000ipg00g200a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虽然片中屡次出现戏剧排练和演出的场景,但《驾驶我的车》不是对戏剧流程的简单再现。
音去世后不久,家福应约去俄罗斯参演国际班底的《凡尼亚舅舅》。第一幕凡尼亚和医生阿斯特洛夫谈论老教授新娶的年轻妻子叶莲娜,她是这俩人暗恋苦恋的对象,凡尼亚有这样一段台词:「她忠实于教授,可惜,这种忠实是彻底虚伪的。在这忠实里有许多空洞的言辞,缺乏合理性。对一个自己不能忍受的老丈夫变心,这不道德;可是极力扑灭自己可怜的青春和活跃的感情,这倒不是不道德了。」
演出中,家福说出「她的忠实是彻底虚伪的……」触及内心痛处,瞬间崩溃,无法继续演出,不顾一切地走向侧幕。这显然是个演出事故了,扮演破落地主伊里亚的演员方寸大乱,哭唧唧地喊起来:「别啊,凡尼亚,我不喜欢你这样。说真的……」这时扮演医生的演员镇定地接上本该是凡尼亚的台词:「闭嘴吧,你这块华夫饼。」如释重负的伊里亚顺势接下去:「凡尼亚,你容我说几句……」演出平稳过渡到下一个章节。
![图片[9]-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e0e4b72dj00r0nt8t000m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熟悉契诃夫剧本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苦涩又滑稽的段落,甚至这里的「阴差阳错」是很有契诃夫式幽默的。但是就电影本身而言,契诃夫在这里不构成观看门槛。
镜头被安置在一个能够看到下场门的观众视角,它不放过侧幕凡尼亚和台上医生和地主的每一丝的应激反应,这些台词以它们字面的意思逼出了演员们赤裸的精神状态,尽管他们其实是在演出中,而他们被突发情况激发的最诚实的模样,似乎刚好是最贴合文本想象的样子。
![图片[10]-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b4f99bc8j00r0nt8t0010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这段情节很快将和后续家福的排练方法论呼应。时隔两年,家福以导演的身份接受广岛戏剧节邀约,为一群说着各自母语的亚洲演员排演《凡尼亚舅舅》。家福训练演员的方式是让他们不带角色想象、不带感情、就事论事地围读剧本。他要求演员忘记「我演的角色是怎样的人物」,而是用最直观的方式朗读文本,尊重字句原本应有的韵律,通过释放语言的多义性让人物重获生命。
这让人联想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的创作方法论:「印在纸上的文字不是它们有生命的样子。不论是对作者还是演员来说,相对于巨大的不可见的创作过程,文本只是很小的可见部分。」戏剧排演的「巨大的不可见的创作过程」,是滨口寻求的「潜在的、不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赤裸世界」,也是他从最初拍摄电影就追求的「让观众无论如何不得不感到震惊的东西」。
![图片[11]-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7877817dj00r0nt8t002nd200u000irg00u000ir.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为了让家福温习台词,音给他录过完整的《凡尼亚舅舅》的剧本,留出凡尼亚的部分。家福坐车时,反复地播放那盘磁带,音的声音在小车的狭窄空间里盘旋,变换着医生、教授、叶莲娜、索尼娅和奶妈的身份。
《凡尼亚舅舅》的剧本支撑起庞大的、不可见的画外世界,熟悉或不熟悉契诃夫的观众,都可以随着滨口的运镜,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经历一次契诃夫发现/再发现之旅。在高槻不能理解排练场上的索尼娅和叶莲娜之间为何会发生感人至深的化学反应时,家福回答他:「是契诃夫的文本把她们带到这里。」
他也诚实地告诉对方为何自己不敢演凡尼亚:「契诃夫的文本让我恐惧,它们拽出了我所不愿面对的、真正的自我。我无处可逃。」镜头前可见的排练和不可见的、理想的演出版《凡尼亚舅舅》,终将揭示这群角色自己都不了解或不敢了解的意识世界。这群以窥探他人、塑造他人、成为他人为职业的演员,终将别无选择地逼视自己。
![图片[12]-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94dd5c51j00r0nt8u000kd200hs00bug00u000jy.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偶像演员高槻曾是音的情人,音死后,为了和她的世界发生交集,他报名参与家福导演的《凡尼亚舅舅》。家福知道高槻和亡妻的私情,他把自己隐秘的妒忌和愤怒,变成微妙的惩罚:让应征「医生」角色的高槻去演凡尼亚,潜意识里,他想让对方因为这个角色,感受自己的煎熬。这确实折磨了高槻,他在排练中屡屡碰壁,持续受挫让他苦闷,他不能确认这是不是家福有意为之的刁难。
「为什么非得是我?」
「你不妨试着交出赤裸的自己,去回应文本。文本是在叩问你,你回应它,它也会回应你。」
家福在酒吧里和高槻讨论的是创作方法论,之后,高槻确实交付了他赤裸的内心:「契诃夫的文本不能在我身体里唤起任何东西,但音的故事可以。」
![图片[13]-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65f5cd9aj00r0nt8u000h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两人短暂同车的段落,是整部影片最核心的段落。他们都仍然爱着音、也都无可奈何地永远失去了她。家福回忆多年前的丧女之痛让音放弃表演,转向写作,但她的创作灵感只在高潮出神的状态下发生,醒来后,她会忘记那些故事,全靠家福的复述。
家福认为,死去的女儿和这些故事把两人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即便音持续出轨,「她背叛我,但她仍然爱我,我从不怀疑这点。」因为恐惧失去音,家福始终缄默,直到妻子猝不及防地死去。
高槻质问他:「你是否想过,她一直渴望向你坦白?」他说起音给他讲过的故事。还是那个七鳃鳗的女孩,故事的后半部分流淌着暴力和悔罪的血液,女孩意外杀死企图侵犯她的入室窃贼,她仓皇逃离,而她一直没得到等待中的制裁,许久以后,女孩再次来到男孩家,发现门口多了个监控探头,绝望的女孩对着镜头告解:我犯了罪。
「这大概是个恶趣味的故事。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就意识到,音在告诉我一些很重要的事。」
「家福,哪怕是至爱的对象,想要完全地窥看对方,那样的追求只能落得自己痛苦。如果真要窥看他人,只能深深地、直直地逼视自己。」
![图片[14]-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fd91c602j00r0nt8v001ud200u000itg00u000it.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如果理性地分析这个段落,高槻是替死去的音控诉:她渴望被倾听,却从未有机会。这显然呼应滨口在《欢乐时光》里就确立的主题,即,女性温柔地警示男性,因为你们不倾听,必将陷入困境和悔恨。但这个段落真正的能量不在于内容的表意,而是,扮演高槻的冈田将生在这段完整戏剧时间里呈现的「面孔」。
![图片[15]-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949775c9j00r0nt8v0011d200hs00bug00u000jy.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欢乐时光》(2015)
「他打开了封闭的门窗。他的话是无遮无拦的心声,那不是表演。」村上的原话对演员来说是个悖论。而我们看到的电影里的这个时刻,冈田进入了一种难以被定义的状态,他的神情里合并了极致的通透和炽热,高槻此前一双缺少底蕴的眼睛,这一刻仿佛有火焰在泪水中燃烧。滨口对此的评价是:「冈田让我瞠目结舌,他的表演超出我的预想太多。」和他演对手戏的西岛在拍摄现场就觉得:「发生了不得了的事啊。」
![图片[16]-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d78c53f6j00r0nt8v000ud200hs00bvg00u000k0.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就像滨口本人承认的,契诃夫的剧作是他借力的中介。他让演员扮演演员,让他们表演表演,在「元电影」的框架中,《驾驶我的车》仍然指向滨口迷恋的主题——在艺术中确认「自我」,现实中迷惘的个体在艺术中寻回主体性。
所以,随着高槻回忆音的故事,燃烧的生命气息注入到那张大理石般的脸庞,在象征层面,他的使命已经达成。他注定要「意外」地错失演凡尼亚的机会,「凡尼亚舅舅」这个角色,注定要由逃避的家福来承担。家福绕过漫长的弯路,他和高槻、和亡妻、和自己艰难的和解,是为了给「凡尼亚舅舅」有始有终的交代。
![图片[17]-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34db8802j00r0nt8w001ad200u000gcg00zk00jc.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舅舅,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许许多多漫长的白昼,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地忍受命运带给我们的考验。我们要为别人劳动。我们受过苦,我们哭过,我们尝尽辛酸,上帝会怜悯我们,我和你,就会看见光明、美好、优雅的生活,我们就会高兴,带着温情,带着笑容回顾我们现在的不幸,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戏中戏的《凡尼亚舅舅》演出现场,扮演索尼娅的聋哑女演员用手语打出这段最经典的台词。在被拉长的戏剧时间里,镜头始终对着凡尼亚,对着家福,保持不近不远的凝视,西岛贡献给银幕一张「无法定义的美好面孔」。
这自然是一个「卡塔西斯」的时刻,但滨口龙介要表达的,比「艺术家的画像」更进一步。下一个反打镜头里,出现了女孩渡利的特写,她是戏剧节组委会给家福安排的司机,每日载他往返于酒店和排练场,她和家福有限的交流,似乎只是在戏剧节的排练进程之外不足道的枝节。
![图片[18]-年度最期待日本电影,比我预期还要好-天时网](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1%2F1008%2F59dde926j00r0nt8w000wd200hs00bug00u000jy.jpg&thumbnail=65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影片颇有意味地结束于司机女孩,这个过早经历太多生活磨难的姑娘,旁观了《凡尼亚舅舅》在舞台上从无到有的历程,她那张一度麻木的脸上,重新染上生命鲜活的气息——现实被艺术救赎,这不是艺术家的特权,也是普通人的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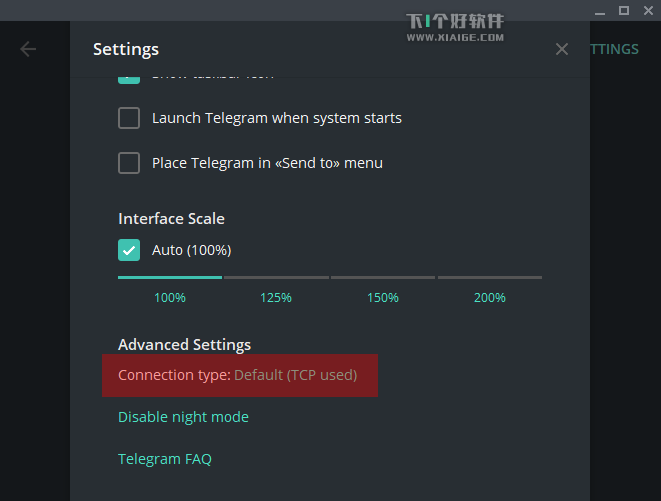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